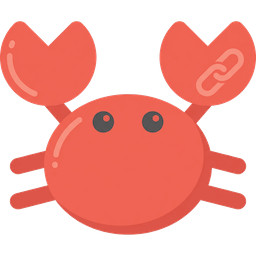《我父亲的影子》:极具自传色彩且含蓄隐晦
英国尼日利亚裔导演阿基诺拉·戴维斯(Akinola Davies, Jr.)的长片处女作《我父亲的影子》(My Father’s Shadow)带有一种强烈却难以捉摸的自传色彩。该片由戴维斯的兄长瓦莱(Wale)编剧,讲述了两位年幼兄弟在尼日利亚1993年总统大选期间的故事。那场选举在经历了十年的军事独裁后,曾为民主带来曙光。电影的第一个戏剧性场景极具记忆色彩,让人隐隐作痛:两兄弟——长兄十一岁,幼弟八岁——在自家门前懒散地消磨时光,吃零食、发牢骚、玩纸刻动作玩偶,试图用俏皮话和虚张声势来填补周围的孤独与寂静。在他们那天无组织且流动的时光中,有一种永恒的童年感,徘徊在梦幻与无聊的边缘,其可能性既因男孩们的想象而扩张,也因之受限。
随着他们的父亲福拉林(Folarin,由索佩·迪瑞苏 [Ṣọpẹ́ Dìrísù] 饰演)的到来,两兄弟的生活以及电影本身迅速进入了行动状态。他离家多时,归期未定,但他这次回来并非为了久留,而是要带男孩们一起坐大巴前往拉各斯,他在那里的一家工厂工作。(他们的母亲因一件略显神秘的差事外出,他们在她回来前便已离开。)这对兄弟来说是一次新奇的体验,他们兴奋的好奇心在眼神交汇中被放大:戴维斯的叙事触觉不仅锁定在角色做了什么,更在于他们看到了什么。他的剪辑手法在观察与行动之间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切分,没有显眼的视觉提示,仿佛是为了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。记忆中的事件感是通过电影对孩童视角的唤起而暗示的,并且在故事深入之后,当幼弟的名字——阿基诺拉(Akinola)被提及时,这种感觉得到了强化。(阿基诺拉由高德温·埃博 [Godwin Egbo] 饰演,其兄奥拉雷米 [Olaremi] 由该演员的亲兄弟奇布伊克·马维勒斯·埃博 [Chibuike Marvellous Egbo] 饰演。)
福拉林带着儿子们匆忙离开,预示着麻烦将至。在巴士旅途中,兄弟俩瞥见乘客报纸上的头条:选举已经举行,但结果尚未公布;有报道称某军事基地发生了屠杀。他们的父亲是反对派候选人 M. K. O. 阿比奥拉(M. K. O. Abiola)的支持者,他与一名支持军政权的乘客发生了争执。(在1993年的选举中,人们普遍认为阿比奥拉已经胜出,但选情并未正式揭晓,近两周内整个国家都在焦虑地等待结果。)从孩子们支离破碎的观察中看,他们的父亲似乎是一名反对派活动家,而他的这次旅程带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目的。
《我父亲的影子》最有力且最具原创性的方面之一是其背景的丰富性:公民和社会背景不仅仅是布景,而是戏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并非解释性的,而是构成性的。大巴一度耗尽了燃油,大多数乘客都满足于等待司机解决问题,但福拉林说服了一位路过的卡车司机载他及其子走完剩余的路程。男孩们对拉各斯一无所知,而在这里长大的福拉林则自豪地向他们介绍这座城市。两兄弟怀着着迷与惊奇的神情,注视着人群、小贩和街头艺人这些平淡无奇的景象。但当载满士兵的卡车经过时,他们也察觉到了父亲的警惕。“愚蠢的人,”他说道。这是政权执法者第一次展现存在感,但并非最后一次,即使他们不在视线之内,他们所代表的威胁也沉重地压在故事之上。这种威胁笼罩在男孩们对拉各斯的体验中,既存在于他们对远方事件的静默观察里,也存在于与父亲的朋友和伙伴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。
电影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一个昼夜之间,政治与个人这两个时钟似乎不同步地跳动着,既紧迫又显失谐。福拉林的政治参与感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,他遇到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(由奥拉罗蒂米·法昆莱 [Olarotimi Fakunle] 饰演),其绰号“走廊”(Corridor)反映了他的体型以及在人群中开辟道路的能力。“走廊”称呼福拉林为“卡普”(Kapo)和“我的领袖”,但他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悲观。他认为现政权正在固守阵地,并称已有四名反对派支持者遇害。男孩们很快看到了另一个头条新闻——“军方否认邦尼营有死亡事件”——随后,当街头爆发冲突时,福拉林仓促带走了他们。
第二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涉及一件紧急的私事:福拉林已经六个月没拿到工资了,他出现在工厂找主管对质,要求拿回属于他的报酬。但主管要到晚班才在,为了消磨时间,福拉林带着儿子们走访了一些朋友和心仪的去处。随后的全城漫游——父子三人和司机挤在摩托出租车上——对福拉林而言,演变成了穿越自身记忆的旅程。他向儿子们展示自己年轻时的旧址,带他们去酒吧与同伴混在一起,并给他们讲述自己当年在街头追求他们母亲的浪漫往事。(一位朋友插话道,这对夫妻曾被视为“当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”。)在一次海中畅游的短暂停留中——这一场景带有电影《月光男孩》中标志性游泳场景的意味——福拉林讲述了一个来自童年的创伤性故事:他的兄长不幸溺亡,奥拉雷米便是以这位兄长的名字命名的。
通过这种方式,阿基诺拉和瓦莱·戴维斯在影片中为兄弟俩建立了两个平行的觉醒过程,男孩们所见所闻的一切——不仅是对话,还有所有的环境印象——都对其中之一或两者兼有贡献。一种是政治觉醒,由围绕选举危机和随后的军事镇压所产生的恐惧气氛触发,这在电影中引发了共享的国家记忆共鸣。另一种觉醒则关乎第二层记忆:家庭记忆。兄弟俩逐渐产生了对父母亲密史的认知,鉴于这是他们自己的背景故事,这种认知便与他们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形象交织在一起。
观众带入电影的所有知识(或无知),以及观众获得的关于制作和制作人的任何信息,都是观影体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对尼日利亚从军事独裁向民主的转型知之甚少,因此仅通过这部电影才了解到1993年的选举是被该国的专制政权废除的。在电影中,就在废除消息公布后的瞬间——当时父子三人正在酒吧看电视——枪声响起。随着拉各斯的街道开始因抗议和镇压而动荡,福拉林匆忙带着儿子们离开城市前往安全地带。我还通过阅读关于《我父亲的影子》的阿基诺拉·戴维斯采访了解到,电影中记忆的展开与他本人的经历如出一辙。戴维斯兄弟远非仅仅描绘他们的童年记忆,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、也为一个他们未曾拥有的父亲创造一个过去。
阿基诺拉和瓦莱·戴维斯的父亲在阿基诺拉(出生于1985年)仅二十个月大时因癫痫发作去世。瓦莱像电影中的奥拉雷米一样,比阿基诺拉大三岁,因此在1993年的事件发生时,他们的年龄与银幕上的兄弟大致相仿。为了这部电影,他们根据记忆、母亲和其他亲属印刻在他们脑海中的家族传说,以及后来对拉各斯的访问,将早年岁月重构为一种“反生活”(counterlife)。戴维斯的导演手法反映了电影主体性所依托的多种线索;影片中最引人注目的场景之一发生在兄弟俩不在场的时候。他们被送往一个关闭的游乐园玩耍,那里年迈的看守人(阿约·里贾杜 [Ayo Lijadu] 饰)是福拉林的朋友。这位刚丧偶的朋友冗长地自责于他对待妻子的方式,在男人独白的整个过程中,镜头一直停留在福拉林的长久特写上,暗示着他自己那些不为人知的婚姻不和与良心责备。
戴维斯和他哥哥所施展的这种“召唤术”带有一种整体性的创造精神,通过电影中细腻观察的细节和将这些细节统一起来的奇特形式,镜像出了关于他们父亲的二手记忆。剧情节奏由闪回帧的拼贴画面调节,这些画面将早期和后期的观察汇聚在 associations 的翻滚中,并暗示了戏剧神秘、幻象般的本质。然而,在一个关键时刻,电影沉稳的主体性使细节脱离了背景,将故事从辛辣的暗示导向了令人困惑的模糊。对于一位在《我父亲的影子》其余部分里将父权唤起为象征权力和物质权力的电影制作人来说,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失策。
撇开这一幕不谈,导演与电影基本素材(他父亲的缺席以及童年早期的政治喧嚣)之间那种侦探式的关系,是他所营造的独特基调的情感杠杆。历史性的危机使得这个个人故事在内在的广袤中产生回响。戴维斯兄弟寻回的记忆产生了一种私人的神话体系,它同时具备家族、城市和国家的属性。尽管《我父亲的影子》具有强烈的主体性,但其非同寻常的力量源于其非人格化的元素——源于那种似乎具备经文般权威的力量,记忆借此被升华为神话,而关系则升华为宿命。 ♦